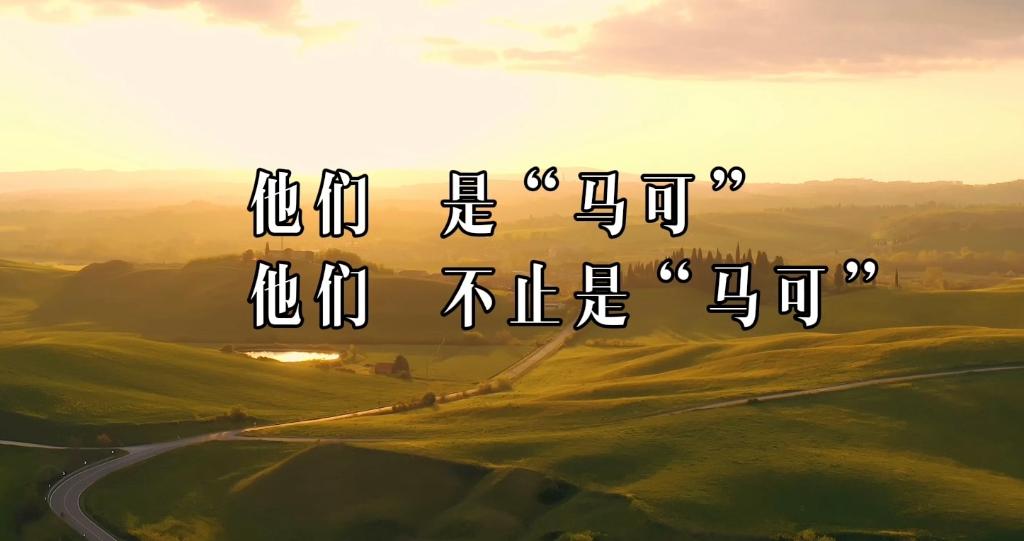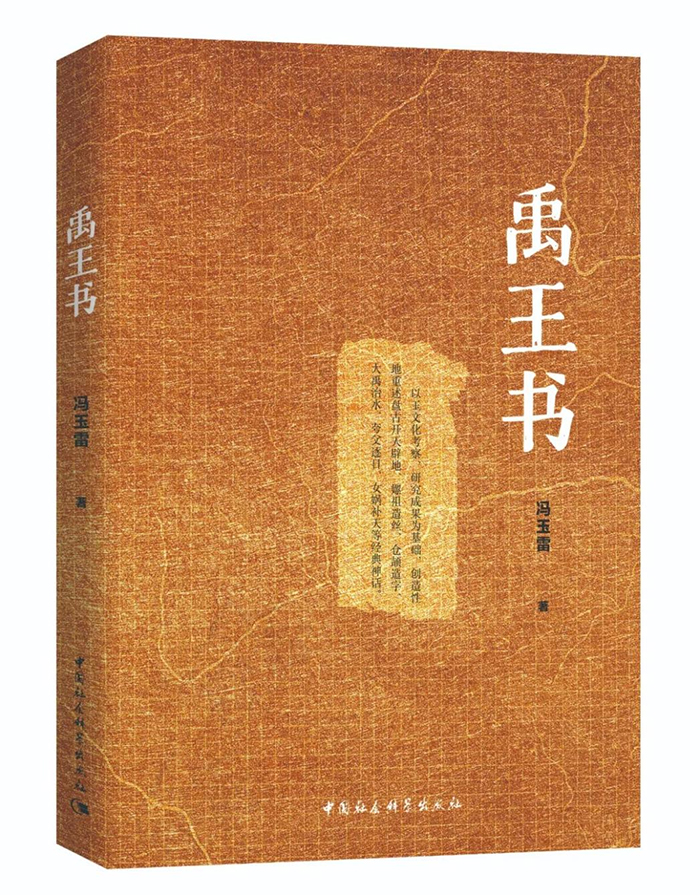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冯玉雷耗时七年(2017—2023)创作完成的集考古、玉文化于一体的长篇小说。《禹王书》通过小说艺术转化考古研究和学术成果,讴歌了贯穿华夏文明发生、发展中的玉文化承载的核心价值和中国精神。小说以古史传说中的圣贤大禹与其妻女娇的爱情故事为主要框架,结合盘古开天辟地、仓颉造字、夸父逐日等众多神话故事和传说,创造性地重述、书写大禹公而忘私、九死未悔的精神。
中国伟大精神的艺术化书写
冯玉雷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就开始发表小说、散文。在那个年代,不少中文系学生都有一个文学梦,难能可贵的是,毕业后,不管工作如何变动,他始终坚持文学创作。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在《飞天》发表两部中篇小说《陡城》和《野糜川》,后来陆续出版长篇小说《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野马,尘埃》及文化专著《玉华帛彩》《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笔记》《敦煌文化的现代书写》(与赵录旺等合著)等。多年来他致力于写同一个题材——敦煌。
作家、评论家雷达认为,《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表达了作者独特的文化情思和历史文化观念。“六千大地”泛指西部大地——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传统上的西域各地及中亚。“六千大地”极言其远,包含一个大文化带,而敦煌是它的一颗明珠。因此雷达在小说序言中评价冯玉雷是“一个顽强的文化寻根者,一个试图‘还原’丝绸之路文明的梦幻者,一个追寻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个执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来建构文字王国的人”。
《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之后的《敦煌遗书》,是冯玉雷写敦煌的第三部长篇。符号学家赵毅衡在序言中说:“《敦煌遗书》确实是敦煌自己的书,冯玉雷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两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敦煌书写。”并且把冯玉雷的敦煌文化题材小说总结为敦煌的“第四次书写”。
以上列举的冯玉雷的创作、研究成果大多完成于他2012年6月履职《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之前,“转行”后,他会不会就此脱离写作?这种顾虑显然是多余的。长篇小说《禹王书》就是一个明证。
看到这部小说的清样,我很激动,为冯玉雷创作的又一次跨越感到高兴。这部小说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禹铸九鼎等神话传说为背景,以最新史前文化考察研究成果为依据,充分展开文学想象,对上古神话进行激情澎湃的“重述”,重塑了禹、鲧、舜、仓颉、夸父等一系列史前人物形象,使这些符号化的神话人物生动可感、栩栩如生;通过这些“形象丛林”,让我们看到遥远的玉文化如何诞生、如何在夏朝汇聚形成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进而影响到礼乐制度。小说无论在语言运用、人物形象塑造还是情节安排上,处处都洋溢着玉文化精神。
叶舒宪等学者依据“四重证据法”研究认为,中原地区玉礼器生产伴随王权崛起而揭开序幕,这个过程中西北齐家文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齐家文化接受东方玉器崇拜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斧为主的玉礼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礼器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将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经过儒家“温润如玉”理念的熏陶,和田玉独尊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华夏文明发生的巨大动力和核心价值。《禹王书》通过艺术手段生动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赋予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经典神话新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把大禹治水与政治治理、女娲补天与道德重建、夸父逐日与职业精神结合起来。冯玉雷对这些经典神话进行了重塑、再造,如他对精卫填海的重塑就别出心裁。在《禹王书》中,精卫不再是怀着仇恨之心衔着石块填海的形象,而是不辞劳苦,用敦煌三危山玉石到东海换水的爱情守护者形象。一开始读到这些情节时,人们可能有些不理解,甚至疑惑,但再三思虑后就会感到:玉文化的实质不就是和谐共处,成人之美吗?想一想,先民创造文字时,带斜玉旁的汉字基本都与“和谐、美好”之意有关。《穆天子传》中提到“束帛”和“玉璧”,二者结合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化干戈为玉帛”。由玉文化孕育出的“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的核心理念,呈现出极强的包容性,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神话的这种重塑就有了重要的文化基础,也提升了《禹王书》的文学价值。
再如,夸父逐日是我们熟知的神话故事。在《禹王书》中,夸父是一个非常独特、非常可爱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悲剧式英雄形象。冯玉雷说,这个人物形象的升华,是在一次考察活动中受到的启发。2017年8月,在第13次玉帛之路考察中,考察队找到并初步确认位于敦煌三危山旱峡的古代玉矿,其开始年代可能早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前后,将中华民族对敦煌开发的历史大大提前,这也表明敦煌之所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因为它是西玉东输最重要的枢纽。这是自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和外国学者大量运走敦煌文书以来,由中国本土学者在敦煌独立完成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探索发现。冯玉雷根据这次发现,在小说中特意将夸父“渴死道中”的地方安排在属于祁连山系的野马南山之北,并且让其化身为三危山和胡杨树,又让三青鸟与精卫鸟的复合体每天往返于大漠与东海之间,送去玉石,带来海水。这种构思极具人文关怀思想。旱峡的古代玉矿让冯玉雷重新审视古代典籍中关于“窜三苗于三危”的记载,把西北齐家文化与东南良渚文化联系起来,如此等等,这些大刀阔斧的创作,都是受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启发,并非空穴来风。
《禹王书》折射出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国精神,讲述的也是贯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故事。冯玉雷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了西北高原般宏阔的大文化书写,正如叶舒宪在冯玉雷、赵录旺合著的学术专题《敦煌文化的现代书写》序言中所说:“张骞来到于阗国的时候,根本没有丝毫提及佛教的内容,只有两种东西引起中原王朝统治者的极大兴趣,这种兴趣甚至驱使汉武帝做出两个非同寻常的举动,都被司马迁如实写在《史记》中:一个是查对古书,为出产玉石的于阗南山命名,那便是在中国文化中‘一言九鼎’的名称‘昆仑’;另一个举动是艳羡乌孙和大宛所产的良马,专门为马而写下赞歌《天马歌》。直到明清两代,这条路上最繁忙的进关贸易物资仍然是玉和马。由此看,敦煌的经卷和佛教艺术都是派生的辉煌,中华玉文化神话驱动的西玉东输和玉门关的确立,才属于原初的辉煌。而将中原文明与西域率先联系起来的西玉东输运动,一定和4000年前西北地区的崇玉文化——齐家文化密不可分。这就是冯玉雷近十年来从敦煌书写转向齐家文化遗迹踏查的内在因素吧。”(本文作者郑欣淼,以上内容选自《禹王书》序言,节选时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