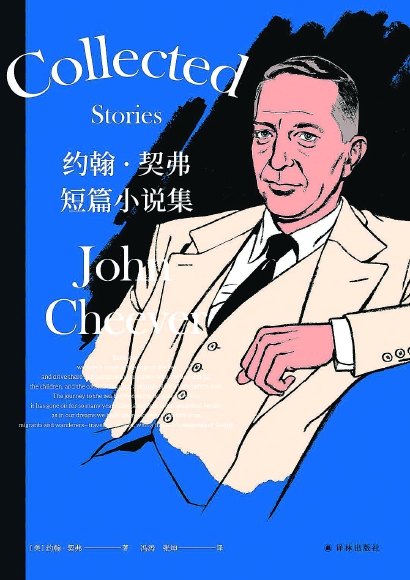
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
契诃夫似乎被约定俗成地视为衡量作家短篇小说写作能力的行业标尺,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作家一旦被冠以“×××的契诃夫”之称,就是对其专业水准的盖戳认证,可他们中的大多数论风格、论题材,其实和契诃夫搭不上边。倒是约翰·契弗被形容为“(北美)城郊的契诃夫”,还算有迹可循——他们视线聚焦的浅薄生活与漂浮的情绪,他们不动声色又登峰造极的“假装日常”的技巧,以及他们在书写中流露的温柔,能隔着漫长的时光和遥远的地理空间产生共振。可是,如果把契弗安置在契诃夫的坐标系里,这委屈了他,因为他并不需要蹭对方的名望。
英国剧作家库瑞什说得漂亮:契弗一直是完完全全的他自己,他以幽默的同情捕捉到生活中意味深长的时刻,他有能力用每一句恰如其分的句子,让一切细节在最后时刻以酒神庆典的方式被升华。
从平凡的世界进入生活的神话
契弗在日记里表达过一种自我怀疑,他顾虑自己的作品“很有局限性”,题材过分狭窄,没有时代感和意见领袖的气质。《阿耳忒弥斯,诚实的打井工》或许可以看作这样一个“跟不上时代潮流的”“逼仄”的故事。阿耳忒弥斯是个打井工,小伙子为了摆脱某个寂寞的中年主妇雇主,找旅行社报了个去莫斯科的团。他刚到莫斯科就被告知,作为“来自西方阵营的劳动者”,他将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去酒店的一路上,他看到“无数肖像在百货店和路灯柱上看着他”。等他浑浑噩噩地坐到莫斯科大剧院里,候了一整晚却没有等到赫鲁晓夫现身,回旅馆的路上,他发现所有的肖像都不见了。第二天,他意外地从一个英国侨民嘴里得知,就在他无所事事坐在剧院里的几个小时里,赫鲁晓夫被废黜。这个傻乎乎的水管工浑然不知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他天真地陷入和一个俄国姑娘的露水情缘中,而对方是一位被斯大林清洗的元帅的女儿。于是,小伙子睡了不该睡的人,被遣送回国。他心心念念惦记着有过一夜情缘的姑娘,和对方频繁通信,竟惊动了两国的安全部门……风波终于不了了之,小伙子再也没有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回信,只是,“他经常想到她信箱上的一小块白漆。天气转暖以后,他听到了具有治愈效果的雨声”。
契弗写过很多个类似的故事,历史的风浪呼啸,但是大是大非大事件和小人物的小确幸小确丧之间,他关心的是后者。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是一种风貌,芸芸众生的悲欢是另一种。他在战后美国中下层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人们生活在心照不宣的宣言中——没有战争,没有过去,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危险和不幸”。推动着社会进展下去的,不是大人物的生或死,而是万千普通人既渺小又膨胀的欲望,他们对金钱和美满生活的渴望,对完美婚姻和爱人的幻想。就像在《那罐金子》里,一对小夫妻从中西部迁居纽约,飞黄腾达的中产梦主宰了他们的人生,大萧条、参军、战事和同伴的死亡都不能中断那不止不休的渴望。然而命运如同阴险的庄家,反复玩弄着这些兢兢业业经营着“更美好生活”幻梦的人们,直到他们被持续破灭的梦想和无法实现的希望拖垮,“失意如同皮鞭,抽在他身上,痛得他几乎晕厥”。“财宝这个词让他悚然一惊,一时间他仿佛看到喀迈拉,看到金羊毛,看到埋藏在彩虹朦胧光晕中的宝藏。”契弗无暇于触摸时代的脉搏,却给无名之辈卑微的发财梦写出惊心动魄的史诗般的结尾,他从平凡的世界进入生活的神话,他所打量的是最微妙也最重要的事:普通人幽深契阔的精神世界。
他呕心沥血地追求着小说的艺术
在《圣诞节是穷人的伤心日》这篇,契弗写了一个在富人公寓里当值的电梯工,他在圣诞节一早就开始和住户们诉苦,絮叨着自己的孤独和委屈,住户们很同情这个穷困的单身汉,于是每户人家都给他匀了点圣诞大餐和礼物,到了傍晚时分,他的小工作间里堆满了美食和各种实用的小件。他因为收获超额的善意,开心过了头,给一位有钱老太太开电梯时速度过快,遭投诉后被当场辞退了。电梯工的一天呼啸而过,如同一个荒唐又蹩脚的笑话,这个寒酸拮据的大叔没有光辉伟岸的形象,他不坏,只是有些鸡贼和猥琐。契弗写得格外生动的就是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猥琐,这其实是庶民欲望里最具有色彩、最值得诚实面对的形态。这篇小说里有一段看似琐碎,实则微言大义的“闲笔”,电梯工“估算每上下一趟大约八分之一英里,他靠开电梯为生有十年了,他已经经过成千上万英里的距离,这段距离足可以使他驾着电梯驶过加勒比海的重重云雾,降落在百慕大的珊瑚海滩。”契弗孜孜不倦写出来的,正是从生活狭窄的电梯井,驶入杳杳云雾的意识世界,直到俯瞰无边无垠的时间。
他对笔下的角色是很温柔的,虽时不时会揶揄那些虚无的秩序和乏味的品位,但从不以优越的智识感去霸凌平庸盲目的人们,也不会抨击他们随波逐流的欲望和梦想。他没有野心勃勃地把文学当作社会干预的利器,在他的认知中,“小说就是个实验过程”。所以他最耿耿于怀的是《纽约客》的编辑赞美塞林格是个“了不起的工匠”,而他没得到类似评语。
确实,比起契弗书写的题材,他对小说艺术呕心沥血的追求经常被低估了。
在《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里,契弗写了一个纽约阔绰之家在乡间度假地度过的许多个夏天,其间发生过阶层错乱的小儿女恋情,也重复着社会壁垒被乡野风光暂时屏蔽的错觉,这些都不重要,社会等级的议题不是重点。这个故事里的人们如同罹患强迫症一样,循环地回忆起某个夏日午后层出不穷的状况,在小径交错的意识流的花园里,时间获得了自由流淌的能量,漂去漂来的岁月像探戈舞步一样交错着,冲破线性时间的约束交织出一支回旋的舞曲。很多年后,垂死的契弗被酒精和癌症折磨得面目全非,他在生命的尽头感慨:一页好的散文足够让作家立于不败之地。那么《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可以看作是“孤篇压时代”的不败之作。其实,无论他同代的评论家怎样非议他,契弗清醒地知道自己写得有多好,在《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初稿写完时,他给《纽约客》编辑的信里颇为自得地写道:“我创作了一部类似回旋曲的作品。”
他在写作艺术层面大胆冒进,甚至因为过于革新而孤独。1972年,《纽约客》退回了《卡伯特家的珠宝》,编辑认为这根本不算小说。然而半个世纪后的敏感读者读到这部伪装成漫游随笔的小说,会惊讶于契弗的艺术实验比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更超前,他在三言两语的篇幅里触及了短篇小说隐秘伟大的秘密:它收容着各种无法进入情节的情绪,随时随地地冲破时空阻碍,诉诸于浩瀚如星空的意识世界。今天的读者应该庆幸契弗留下了《卡伯特家的珠宝》,留下这么多无法被归纳的趣味盎然的短篇小说,它们是小说艺术中异常贵重且璀璨的“珠宝”。(记者 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