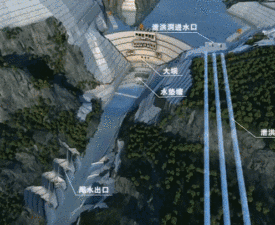《回响》 东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初读《回响》,女刑警冉咚咚受命调查“大坑案”,会误以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标准的推理小说。但随着情节的深入则会发现,小说原来由两条叙事线构成,一条是案件推理,另一条是主人公冉咚咚的婚姻危机。借用作者本人的话,“奇数章写案件,偶数章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两条线上的人物内心翻滚缠绕形成‘回响’。”因此,读者就不能把《回响》视作一部标准意义上的推理小说,而毋宁称之为一部推理小说的“变体”。
近年来推理、犯罪、侦破等叙事元素对“纯文学”的浸润已经不算一件新鲜事,且不说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郑执《生吞》、石一枫《借命而生》等都有着颇高的话题度,稍早一些的作家如麦家、须一瓜、弋舟等的作品中,也都有悬疑推理色彩。“推理小说”作为原先主流文学视野中一个相对偏僻的通俗文学种类,逐渐成为作家们跃跃欲试、希望借此一展才华的“爆款”形式。《回响》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这一趋势。
如文化批评家詹明信所言,后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通俗文艺、亚文学已经普遍泛滥,且其形式因素已经不再仅被当作材料“引入”文本之中,而是彻底结合进“纯文学”,进而形成某种真正的杂交本体。但小说读者仍然能从那些以严肃态度创作出来的、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作品中获得充分的伦理共情和阅读乐趣。因此在《回响》这里,读者首先关注的,是作家如何借用了“推理”的叙事元素,以及这种叙事元素对文学创作本身是否适用的问题。
有评论者从“心理现实主义”的角度解读《回响》,其通过将心理探寻与推理过程结合,叙事特色即在于心理推理。所谓心理推理,指向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整部小说的叙事推进过程中,主要人物的心理隐疾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并影响着人物活动的轨迹和动机,甚至在有些时候,上述心理隐疾还会被拿出来当作小说本体性的问题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一系列心理方法的运用又成为找出凶手的实际工具。
如书中幕后“BOSS”徐山川就患有一种名为“简幻症”的怪病。所谓“简幻症”指的是对现实抱有简单幻想,希望世界保持原样的强迫症,在徐山川身上则意味着拒绝心理成长、只想停留在婴儿期的一种特殊心理。而徐山川在性方面的放纵,实际上也来自于想将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彻底征服的控制欲。这个经常叫嚣“不信钱砸不晕你”的公子哥儿,由于父亲的投资才得以发迹,加之他的母亲又是干部,且其本人瘦小、丑陋,难免在童年时期留下心理阴影。在掌握资源以后徐山川对貌美女性的渴求,自然变成了一种逆反式的补偿。这种补偿背后隐含的是现代文明压抑。
弗洛伊德在《“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一文中,对文明的性道德与自然的性道德进行了区分,弗氏将文明视为自然的对立面。在徐山川买凶杀人的这条犯罪链上,文明的压抑及与之伴随的资本异化,将人普遍地投入到一种“变态”的境遇之中。而另一条线,冉咚咚的人格偏执与精神妄想、慕达夫因父母控制而对“套路”的极度厌烦等,也有着文明规训对人性压迫产生危机的前兆。
当然纯从小说技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心理推理,同样成立。将叙事线分成两条的好处在于,冉咚咚在追问丈夫时产生的心理压抑对案件调查的紧张气氛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书中冉咚咚因精神压力过大选择以割腕的方式体验凶手的作案心理,读来令人胆战心惊。此外,由于作案人本身的手法并不复杂,因此根据推理人与读者的“均等线索原则”,作者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必须设置一个个有待击破的心理防线,以作为推理人行动过程中的障碍,也即心理推理在客观上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
最直接的通过心理学断案的技巧在小说中同样有体现,最鲜明的例子一个是,冉咚咚通过伪造的夏冰清带血的内衣诱使徐山川承认了自己的强奸行为。另一处则是在小说的结尾,冉咚咚通过点出徐山川的女儿实际是他的妻子和健身教练出轨生下的事实,将沈小迎的心理彻底击溃,并最终交出了自己丈夫的犯罪证据。
作者看上去是在写一本推理小说,但他实际感兴趣的是这一推理外壳下人性的危机与伦理的崩坏,这就使得《回响》与传统的推理小说区别开来。
小说中的两条线实际上可以简化为两组伦理关系,在小说的第七章,作者通过卜之兰的供词成功地将两组伦理关系联系到一起,至此两条线变成了一条线。作者的处理显然是先锋性的,他并不尊崇于常规的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设定,好人未必好,坏人也未必坏。另外,作者还作了男性角色与女性角色的地位“颠倒”,男性看上去强大实则脆弱,女性看上去软弱但更成熟。
无论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这样的设定都有其深刻性,因为它恰恰对应了当下社会的某种现实,即两性关系或更普遍的社会关系正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一个人的境遇不再仅根据他的性别身份或所占有的社会资本直接决定。同理,一个人幸福与否,也不再与金钱、地位直接相关,后者仅是影响因素之一,而幸福牵扯着更为复杂的心理状态、伦理情感等方方面面的东西。
从《耳光响亮》开始,作者就致力于探讨现实、人性、伦理中的一些根本问题。通过推理小说的形式,作家持续思索的文学核心问题再次以相当精彩的方式呈现。无论从小说最终的完成情况,还是作家求新的勇气来看,都值得高兴。(蔡岩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