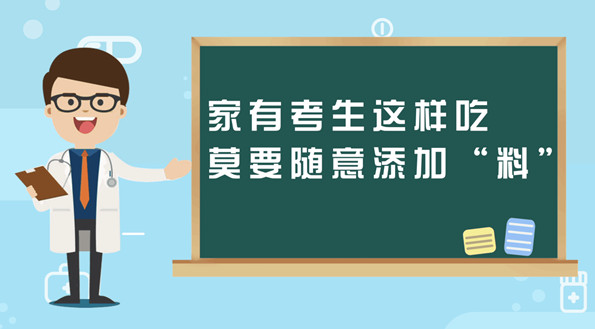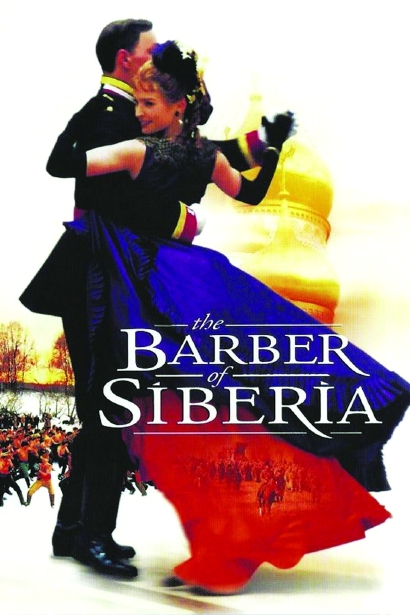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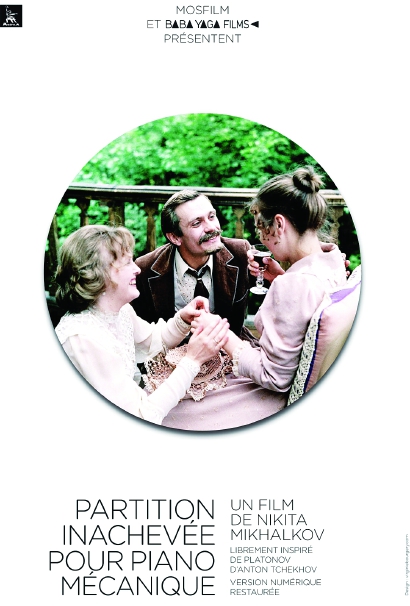

《西伯利亚理发师》海报
宁静的奥勃洛莫夫卡庄园,一个阳光和煦的早晨,小男孩伊里亚·伊里奇在一座深宅大院中醒来了,公鸡报晓了,摄影机从一个物体移到另一个物体。突然,它停在一座钟上,公鸡的啼鸣和钟摆毫无生机的摆动象征着两位主人公截然不同的性格,也隐喻着两人代表的不同时代。
这是影片《奥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几天》的开头,标准的米哈尔科夫式的电影美学:诗意、留白、举重若轻,只消寥寥几个画面,就把原著小说那无以名状的部分,用视觉形象准确地表现了出来。对一些人来说,文学作品在进行电影改编时,经常要面对那些内在的、难以视觉化的、舍弃了就失了余味的重要段落,而这些从来就难不住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这种才能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已显露无疑。
近期在沪举办的“俄罗斯电影大师展”上,可以看到米哈尔科夫的两部半作品。《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和《奥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几天》是他早期的代表作,而《残酷的浪漫史》则是他作为演员与梁赞诺夫合作的。据说普京曾因米哈尔科夫的一部电影而流泪,看哭他的是《十二怒汉》。这位充满浓厚人道主义精神的导演请了俄罗斯当今最顶尖的12位男演员共同主演了这部影片,当然,该片也推他走向了《西伯利亚理发师》后的又一艺术高峰。
俄罗斯文学和戏剧,滋养了米哈尔科夫的艺术
米哈尔科夫生于1945年,与同时代其他俄罗斯名导不同,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既不是塔可夫斯基式的个人独白,也不是对好莱坞的模仿,而是立足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土壤,追求国际性与民族性、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完美平衡——要说与他这种风格最为接近的大师级人物,可能要属斯皮尔伯格了。米哈尔科夫的《西伯利亚理发师》《中暑》等电影,曾先后来到中国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我们从他几乎不去触碰历史本身,但又不割裂历史的影像中,能清晰地触摸到俄罗斯味道,俄罗斯民俗,俄罗斯民族在历史的巨轮下走向了何方。这点在《西伯利亚理发师》中最为明显:虽然变迁无可避免,但脚下这片土地,就像西伯利亚苍翠的森林一样,永远都有生机盎然的时候,这是米哈尔科夫作品中永恒的主题。
从这次影展可以看出,米哈尔科夫的早期创作,无一例外地得益于俄罗斯文学和戏剧,契诃夫、冈察洛夫们“滋养”了他,而他的二度创作,则赋予这些文学名著以接续当代的意义。他自编自导的《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和《奥勃洛莫夫一生中的几天》,前者改编自契诃夫的剧本《普拉东诺夫》和他其他几部小说,后者则改编自俄罗斯著名作家冈察洛夫的同名小说。
银幕上的奥勃洛莫夫实现了对原著的精神超越
说起奥勃洛莫夫这个人,那可是俄罗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多余人”,此人长年蜗居在彼得堡,不从事社会活动,也不从事力所能及的任何劳动。他不关心自己的土地,在农村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他却还留恋着过去,对新的变化一无所知,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面对庄园连年歉收,因交不出房租而被房东勒令搬家等生活中的烦心事,他怎么办的呢?奥勃洛莫夫穿着睡衣吃过午饭又躺回了沙发,带着给管家和房东写信解决难题的决心,他……又睡着了。
冈察洛夫以手术刀般的笔法,对不思进取、耽于空想的人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影响有多大?小说完成后,即被同时代批评家认为“这个人物是解开俄罗斯生活中许多现象之谜的关键”,屠格涅夫曾评价说,纵然到了只剩下一个俄罗斯人的时候,他都会记得奥勃洛莫夫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一百多年后,为什么今天的人们要看这样一个俄罗斯经典文学形象呢?把他搬上银幕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米哈尔科夫是怎么做的。
电影一开场,成年奥勃洛莫夫的生活状态是这样闯进观众视野的。瞧!他就在画面正中央的沙发床上,被厚厚的被子盖着,只露出半个脑袋。没人知道他这么睡了多久,就好像一直要睡到死一样。是不是有点眼熟?嗯,每个宅男宅女都能在奥勃洛莫夫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吧?350个农奴的主人,这是奥勃洛莫夫的资本。而今天的宅男宅女,可能有别的资本,总之大家都饿不死。起床多么累,出门去找谁?纵然有一百个理由让一个懒癌晚期患者走出门去,但最后通常都败在一件事上,那就是从床上起来。
原来这种典型人格,在冈察洛夫的时代到现在从未变过。他们总在等待着一种被人安排好的生活,总嫌生活无趣,却从不反思一下自己能给别人带来什么趣味,或主动在生活中创造什么趣味。如今的社会也是如此,一机(手机)在手,永远不愁会寂寞。
从这点有趣的共性开始,米哈尔科夫着手对100多年前的冈察洛夫进行一次精神超越。
这种超越体现为在精准把握原著主旨的前提下,在冈察洛夫批判反思精神的基础上,在弥漫全片的诗意中,对奥勃洛莫夫这个人(这类人)给予更多的同情与理解。
影片将奥勃洛莫夫的性格纳入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传承谱系。整部影片贯穿了童年和现在的奥勃洛莫夫两条叙述线,童年作为回忆、梦境与成年叙事形成微妙的映照。面容温柔的母亲、玩伴的笑容、午后酣睡中的仆人、毛色油亮的马匹,还有那葱郁的草场和山峦,促成了奥勃洛莫夫一生对于美、质朴、正直和纯真的向往,这也是他现实受挫后慰藉心灵的精神家园。
于是,我们看到了奥勃洛莫夫的“宅”与“软弱”,在米哈尔科夫镜头中,几乎变成了对沙皇时期贵族社会虚伪世故的主动弃绝。他真诚地关心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宁愿在假想中接近内心的真实,他的心灵是孱弱的同时也是深刻的,他最后对自己所爱姑娘的放弃,是软弱也是善良的。
施托尔茨:奥勃洛莫夫的“另一个自己”
与此同时,电影对奥勃洛莫夫的挚友、小说的另一主人公施托尔茨的描写,则另辟蹊径。施托尔茨决意改造奥勃洛莫夫的生活,迫使他跟他一起出席政商名流的各种聚会。这个有着一半德国血统的家伙,与奥勃洛莫夫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积极肯干、锐意进取,对身材与健康进行一丝不苟的管理。奥勃洛莫夫真诚地喜欢、信任他,甚至依赖他,并爱上了施托尔茨介绍给他的女子:奥尔加。而这个贵族小姐也对他芳心暗许。影片最后,他对奥尔加的放弃是出于爱,在奥勃洛莫夫的逻辑里,只有他完美的朋友施托尔茨才能配得上完美的奥尔加。
某种意义上,施托尔茨就是奥勃洛莫夫耽于行动无法实现又希望成为的“另一个自己”,奥尔加嫁给施托尔茨其实也就是嫁给了奥勃洛莫夫的理想自我。如此一来,奥勃洛莫夫再次获得了心灵的平静。在影片尾声画外音的讲述中,我们得知奥勃洛莫夫又回到了他的沙发,并最终死于中风。
或许,那个在田间山头与施托尔茨和奥尔加骑着三轮车飞跑而过的奥勃洛莫夫并不存在,又或只存在于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无限追念之中。影片用非常明亮的色调呈现了这一段落,要知道冈察洛夫的原著小说并没有这一段,这是米哈尔科夫作为编剧之一,对小说和人物的再创作,它像极了特吕弗的《祖与占》中三个好友在桥上欢奔的段落,浪漫得快要起飞,美好得近乎不真实。
在米哈尔科夫看来,在奥勃洛莫夫以荒废一生为代价,拒绝心灵蒙尘的反衬下,施托尔茨忙于世俗的性格多少有些无趣。当人类在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像施托尔茨那样沉浸在忙碌的日常中,往往不再保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基于这样的认识,影片中展现了施托尔茨的分秒必争,他的不虚度时光,信奉活着要有所作为。有一场戏,是两位好朋友在蒸俄罗斯桑拿时,对树与树根进行了一段富有哲思的对话,这段戏看似闲笔,却体现了导演的功力。从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关于所有的世俗欲念,奥勃洛莫夫从未艳羡,他的人生既无诗意,亦无光芒,但却是他理想的羽衣,沉淀于似水流年的嗟叹之中,成就了他碌碌无为的美满;但施托尔茨对这些没兴趣,他早已冲出房门,扑进了彻骨寒冷的冬雪之中……
如果说伊凡·冈察洛夫用小说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典型的人物,那么米哈尔科夫则用电影语言完全地展现了奥勃洛莫夫的灵魂。银幕上田庄的自成一派、房间的凌乱尘垢、树林的幽静沉默、雷雨的激情澎湃,无不是奥勃洛莫夫心灵的显影。
当镜头跟随着主人公在田庄老宅里游走,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纯粹,镜头“望”向奥尔加光洁后颈和耳畔被风吹起的可爱绒发,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纯真和深邃。这当然是米哈尔科夫的一次超越:伟大作品可以如此意味深长,可以超越历史和时代,从作者所处的当下出发,打动后世的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