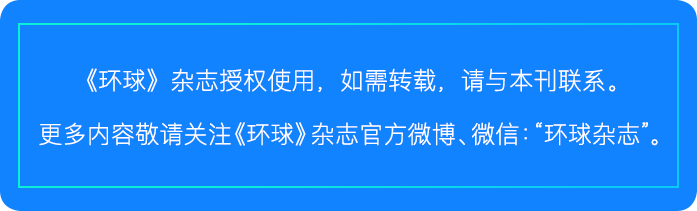巴以冲突再塑中东

5月5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一名妇女抱着孩子站在建筑废墟旁
文/钮松
编辑/吴美娜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爆发。在1948年因以色列正式建国引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以之间迄今近80年的冲突与博弈历程可谓跌宕起伏。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延宕数月。这一背景下,红海危机也频频成为热议话题,冲击波及全球。5月,巴勒斯坦入联获得更多推动力;近来,多国抗议美国或以色列的活动此起彼伏。
此轮巴以冲突延宕多时说明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出路何在?这些问题,促使国际社会进一步深思中东地区乃至国际时局。
说明了什么
从重要时间节点看,2007年6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独踞加沙地带以后,巴以大规模冲突日益频繁。不仅巴以关系逐步演进为以色列、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和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之间的“两国三边”关系,而且巴以冲突在军事对抗方面很大程度上主要呈现为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国际舆论中出现了用“哈以冲突”来描绘新一轮巴以冲突的说法。
巴以冲突这一“老问题”仍蕴含着巨大能量。巴以冲突作为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最棘手且仍未能得到根本解决的世纪难题之一,呈现出周期性高烈度对抗与日常性低烈度冲突相交织的基本样态。
巴以冲突的延宕,也反映出巴勒斯坦内部分歧,以及错综复杂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关系。2007年6月以来,尽管法塔赫与哈马斯进行过一些谈判并表露过和解意向,但双方关系并未实现根本性突破。以色列利用巴勒斯坦两派矛盾,主要采取基本稳住法塔赫、集中力量打击哈马斯的斗争路径。
从那时起,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周期性激烈碰撞不断,但这种高烈度对抗往往在数周内便会归于平静,双方长期以来在冲突的把控上存在着某种默契。2022年底,内塔尼亚胡通过组建囊括主要右翼与极右翼政党的六党联盟政府,得以重返总理宝座,该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也因此受到右翼势力的强力塑造。
2023年新年伊始,以色列首任国家安全部长、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本-格维尔进入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广场,此事瞬间点燃巴勒斯坦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怒火。本-格维尔之举成为内塔尼亚胡新政府巴以政策的一个注脚,即继续在巴以关系中不断越过“红线”,其根本目的还是掏空“两国方案”,使巴勒斯坦人的建国梦化为泡影。
当前,以色列政府宣称以“解救所有人质”和“彻底消灭哈马斯”为其在加沙军事行动的两大目标。由此可见,只要哈马斯继续存在,以色列便有延续战争的“自说自话”式的理由,从而为战时内阁续命。
冲突延宕至今,也说明国际社会在促使巴以停火止战上,仍难以形成期待中的合力,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巴以安全治理上的主要缺口。

1月12日,人们在也门首都萨那参加游行,谴责美英两国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的空袭
就在此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后的2023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就巴以相关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尽管美国、以色列等国投了反对票,但决议最终仍以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获得通过。此次决议,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方立即实行持久和持续的人道主义休战。
但美国不断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以停火的问题上唱反调,使得决议难以执行。今年3月25日,安理会通过2728号决议,要求斋月期间在加沙地带立即停火,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停火。这是自此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安理会首次通过要求加沙地带立即停火的决议。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安理会成员在当天的投票中对该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美国投了弃权票。美国仍然维持对以色列的基本支持。该项决议最终也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不仅如此,4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对一项建议联合国大会批准“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由于美国行使否决权,草案未能通过。
至此,尽管中东域内外国家在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上做出了不懈努力,但这还远不足以对冲突进行有效干预。
改变了什么
此轮巴以冲突持续时间之久和伤亡人数之巨,都已超出国际社会特别是巴以双方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冲突的延宕不仅深度搅动了中东局势,也使得以色列的国家形象进一步破碎,一些欧洲国家不惧美国压力公开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些对中东国际关系、巴以关系、美欧关系等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效应日益明显,主要体现在区域和领域两个层面。
区域层面,表现为在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红海周边地区及中东域外等地关联冲突频现;领域层面,主要表现为对中东地区格局演进和中东国家发展利益上的联动影响,中东国家与以色列关系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态势,以色列邻国和地区经济贸易受到冲击。
此轮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伊朗与以色列的阵营化冲突。尽管阿拉伯国家对本轮巴以冲突表达了关切,但总体上仍保持了相对克制。与此不同,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表现出强烈的对以色列抗衡态度。可以说,此轮巴以冲突是中东局势演进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以色列曾在国际社会面前塑造良好形象。比如,不断强化己方因纳粹大屠杀,乃至“犹太人流亡2000年”的受迫害者形象,同时放低姿态来争取他国同情与支持;再如,以色列在缺乏自然资源且“强敌环绕”的不利情形下不断发展壮大,在高新科技及创新发展上有很强的竞争力等。
但以色列在此轮巴以冲突中表现出的对使用军事手段的偏执和一意孤行,使其国家形象凸显恃强凌弱的特点,南非和沙特等国谴责其在加沙的行径为“种族灭绝”。
不仅如此,5月10日,在第十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建议安理会重审巴勒斯坦入联申请时,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用便携式碎纸机当场粉碎了联合国宪章小册子的封面。5月29日,以色列议会预读通过两项法案,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定性为“恐怖组织”。观察人士认为,以色列不断挑战的是国际社会底线,但最终难堪的仍是它自己。
长期以来,欧洲国家特别是以法德为代表的“老欧洲”国家因历史原因,对打击“反犹主义”不遗余力;美国则从美以特殊关系出发,不断在巴以问题上加大对欧洲施压。但如今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态度和加沙地带的惨状,使得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选择承认巴勒斯坦国。
早在2014年10月,瑞典外交部便承认了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近10年后,新一轮巴以冲突促使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等效仿瑞典,分别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公开宣布,已“完全准备好承认巴勒斯坦国”,但会在“一个有用的时机”;另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乌克兰承认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并呼吁结束加沙冲突。
可见,在中东政策上,欧洲国家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未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也很有可能表现出政策自主。
核心问题未变
虽然此轮巴以冲突在许多问题上与以往冲突有所不同,但内核问题依然未变。比如,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地位、巴以双方不断累积的敌意,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等。
近年来,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然而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延宕及外溢效应,令国际舆论不得不直面问题的本质,即巴勒斯坦问题依旧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中东问题涉及与之充满联系又有所区别的阿拉伯世界体系、中东国际体系、伊斯兰国际体系,以及这些体系之下的子系统。巴勒斯坦问题不变的核心地位、根源性地位,为思考此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效应,以及展望巴以和平前景,提供了体系化的努力方向。

5月10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联大主席丹尼斯·弗朗西斯(左)落槌宣布决议通过,
认定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巴勒斯坦问题牵涉巴以冲突、阿以冲突等多重矛盾,并从地缘上搅动了整个中东局势且形塑了中东地区新格局。从此意义上来看,其他中东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的“衍生物”。
新一轮巴以冲突所呈现的依旧是对抗,这其中累积的不仅是冰冷的伤亡数字,更是双方间与日俱增的仇恨与敌意及令人担忧的仇恨代际传递。尽管以色列对哈马斯有着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不论是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标,还是哈马斯“消灭以色列”的目标,实现并不容易。
美国一如既往对以色列的公开偏袒与“撑腰”,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增加了底气。以色列国的成立,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力推有着莫大关系。尽管此后美以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仍是主基调。且美以均给哈马斯贴上“恐怖组织”标签,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描述为“反恐”行动。
从中东地区阵营化对抗的角度看,美以将哈马斯视为伊朗阵营对美、对以博弈的重要一环。在巴以关系中,美国的基本态度是“挺以压巴”;在法塔赫与哈马斯之间,美国的选择是“拉一个、打一个”。这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敢冒道义受损风险在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投票问题上,坚持站在以色列一边。
近年来尽管美国不断减少在中东的军事投入,继续其战略东移,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撤出中东。对美国而言,这只是其战略战术上的调整,中东对美国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此外,虽然国际舆论有“唱衰”美国之声,但美国在中东仍具有明显的掌控力和影响力。美国还利用它在中东的盟友体系,在巴以冲突上,为以色列最大限度减轻来自本地区的压力。
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最新动作是,5月31日,总统拜登公布了一项旨在实现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并确保被扣押人员获释的新提议。他在讲话中提到,这项提议将“在加沙地带创造一个没有哈马斯掌权的更好未来”。按照拜登的说法,这一“全面新提议”是美国与以色列、卡塔尔、埃及和其他中东国家多轮外交对话的产物。不过,多家媒体在报道中提及,相关方过去数月围绕多份类似的停火及“放人”三阶段方案展开谈判,但都以失败告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