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空间越多,人们对它的需求就越旺盛。很难理清公共空间数量的增长与需求的强烈之间的逻辑联系,他们像是互不认输的追赶者,彼长不是为了此消。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共生一起推动了城市的良性生长。 与便利店的社会形态节点的功能不同,城市里的大多数公共空间几乎都是无意识连接的,它们单独立项的时候虽然考虑了自身的处境和社会需求,不过极少有公共空间像便利店那样有一套可以串联的标准系统。大多数城市的公共空间是自由的、松散的,它们像山地里的野花一样随风生长,只有在一定的范围内承担起完善城市服务的功能。 正是因为公共空间出现的自由、生长的随意,没有规制化的约束才让它们有了尽可能鲜活的生命力,它们一方面完成自己的本分工作,另一方面,它们又能够补充其他公共空间负荷过重的问题,这时候,它们的兼职身份胜过了专职的功能。说的粗糙一点,有时候,每一个城市公共空间都可能成为春运拥挤时段的临客、餐车,承担起疏导分流的任务。 |
||
 咖啡馆是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形态,咖啡馆越来越密集,仿佛它们并不担心生意的冷淡。在青岛这座城市,咖啡可以追溯到开埠之初的1897年,当然,曾经历史场景中透露出的只可能是咖啡的涩苦,而非现代商业繁华之下的焦糖味儿。 2007年11月14日,青岛文史学者李明在八大关喝咖啡,古老房子里暗淡的光线和可以感知的寒意成为他写就《一杯咖啡里的青岛史》的起源。他把时间指针回拨到1897年,让李鸿章、翁同龢、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悉数出场,让一座城市的历史与咖啡发生关系,他直言"青岛的咖啡宿命,并非戏言"。 我个人愿意相信这种历史对接的真实,一杯咖啡,一杯茶,甚至是一杯威士忌,这些偶然都足以让一座城市发生命运性转折。当然,有这份冲击力的不只是杯中的咖啡、茶和威士忌,更核心的力量则是那只杯子所处的公共空间。对改变历史而言,公共空间从来都是漫不经心的,在它们从来没有做好(做足)准备的时候,城市、人、生活瞬间就被改变了。 与历史相比,现在更加浮光掠影。青岛像很多城市一样,城市的公共空间布满了咖啡馆。 |
||
 再一次见到王妍是在一家星巴克,她原来在我工作的写字楼上班,每天出入大堂都可以见到她,有一段时间不再遇见,这次见面才知道她换了工作从房地产物业管理公司到星巴克。我点了一杯咖啡,她大概没有认出我。 因为变换了空间,再一次确认人与人的相识就变得困难起来。公共空间从来不具备人像确认的功能,置身其中,所有的行为都是漫不经心的,这与公共空间自由松散的生长形式别无二致;所以,公共空间里发生怎样的事情都不意外,它既保证有充足的、多元的可能性,又无法确保一件事情的二次出现。 我不愿意使用创新这个词语,因此我习惯用它的反面进行表述——标准化乃是停滞之母。城市的公共空间自由松散恰恰避免了标准化,与之相似,城市里的咖啡馆也在极力避让标准化,与城市整体的公共空间的随意不同,它的与众不同更刻意,更带有更强烈的私人化的不限于人文的情怀。于是,咖啡馆像个异类,在经济中低速增长的中国,咖啡馆不仅没有像很多企业那样举步维艰、束手无策,反而对经济充满了好奇,它照例以自由松散的方式落地,不依靠任何组织,只是自己照顾自己。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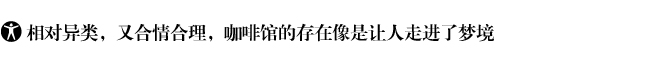 在中国,关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讨论,最常见的论调就依靠规划,似乎规划是保障公共空间数量充足、功能充分的唯一条件,几乎忽略了规划所带有的不可脱离的约束。事实是,公共空间的生长敏感且多疑,外力的过多干涉会影响它的生长能力甚至是成活的可能。 相对异类,又合情合理,咖啡馆的存在(包括那些标准化的咖啡馆)像是让人走进了梦境,走进了一个与城市节奏恰恰相反的场景,尽管很多次我在咖啡馆看到了补课的学生、算计的商人以及各式各样的鼎沸喧哗,可是,更多的时候,有心人把它当成一座城市的缩影。 当然,一个或多个咖啡馆无法陈述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但是,这并不妨碍更没有遮掩城市公共空间漫不经心的特性。只管享受这些为数不多的像山间的野花那样自由生长的松散吧,不需要试图用自己的理性去修补那些自认为不太合理的公共空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