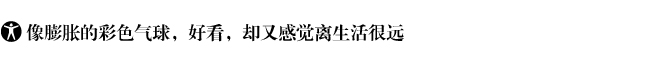 与探讨乡村的未来相比,谈论城市的未来显然更容易,尽管城市的经验值远远低于乡村。 两个月前,我开始在北京短暂蛰居,冒着亲朋好友对我丧失兴趣甚至生厌的风险,我几乎每天都把吃喝拉撒这些再平常不过的生活体验发布到朋友圈,那些图片和文字的结合放大了我在北京的单一生活方式,它们就像膨胀的彩色气球,好看,却又感觉离生活很远。 前不久,在一次电话里,我与康师傅聊起这种想象力过度的问题,线条状的表象当然不能表达我初入一座城市的全部,但其中仍然有可以窥探生活意识的蛛丝马迹。 这是涉及融入一座城市态度的问题,或者说,怎样才是真正地接纳城市和被城市所接纳。对于此,我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说法来自我的一位同事,一天午饭后我们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他在鲜艳的有些刺眼的中国梦的花篮之下自拍,他说他到哪里都不见外,都觉得自己是家里人;一种说法来自崔健,他说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一直不知道"到底要使出多大的力气"。 |
||
 以我的性格和生活经验,我倾向崔健的"外人"说。我很难与一座城市亲近,直到现在,我也是几乎用尽了青春的全部力气才答应自己接纳青岛(至于是否被青岛接纳不属于我考虑的情节),把它定义为我的第二故乡。 人与城市的融合当然有人的行为,其中,人的态度尤其是改变自我、改变世界的梦想、力量甚大,并且这种力量像病毒一样,它传染性太强,人又略显柔弱,稍不留意,人就成了手无寸铁的自我试验品。逃离北上广就是再直白不过的例子,要么梦想照进现实、要么梦想和现实对立的经渲染而成的张扬情绪常常掩盖了生活本身。 但是,这很容易背离接纳的全部内容。一方面,人通过自我救赎或放逐与城市握手言和,另一方面,城市的接受作用却被忽视了。只不过,城市对自我的突破还不够,如果它能够从自己的地方性中跳脱出来,城市是可以以它的优雅、它的轻浮、它的狂欢、它的内涵、它的快乐和悲伤、它的欲望和观念定义一种城市美学。 有时候,城市的封闭又十分微妙,以至于很难察觉,比如地铁的延伸,比如空间的扩展。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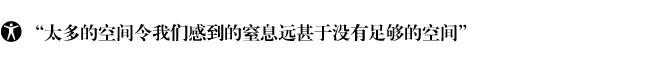 对了解城市而言,地铁虽然快捷,却是最不好的办法,同样,越摊越大的城市空间也妨碍了人和城市的全面互动。部分意义上,地铁也是城市空间的扩展,它虽然促成了人与城市的开放式接触,但是它又是封闭的。 如果说地铁的空间特征会产生属于封闭症候中的幽闭恐惧症,那么,在庞大甚至臃肿的城市空间里出现的就是旷野恐惧症;并且,"太多的空间令我们感到的窒息远甚于没有足够的空间(by苏佩维埃尔《万有引力》)"。 除了空间以外,人和城市还有更多可能的相处方式和接纳方式,所以,把城市面积的扩大和空间的拓展划归到城市的开放和接纳并不准确。的确,城市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可是,如果不解决城市里隐蔽的封闭元素,即使空间的表象解释了开放,它依旧是封闭的意义。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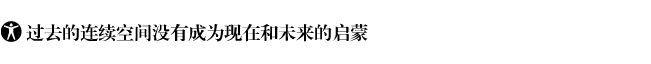 1950年代,北京城墙决定拆除的时候,梁思成、陈占祥提出在老北京城的西侧建立一座新北京城,以经过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广安门的四条东西干道把新旧两座北京城挑起来,这就是被后世称为梁陈方案的挽留北京城墙、挽救北京旧城的整体规划《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最终,北京的城墙还是拆除了。北京变得越来越大,它仿佛成为了一个想象的城市或者说城市的缩影,一切都朝向梁思成声嘶力竭的反向狂奔而去。其实,梁思成的建议和方法早就出现在了巴黎,可惜的是,过去的连续空间没有成为现在和未来的启蒙。 1676年,路易十四决定拆除巴黎的蒂埃尔城墙,他把城墙占用的空间改造成宽广的大街、建成林荫大道,后来这些城墙的位置成为了巴黎最流行的公共空间。巴黎的城墙虽然被拆除,但是原地建成的林荫大道在拓展城市功能的基础之上继承了城墙的分隔性。它让巴黎固有的城市边界没有任何改变,却促成了一个规模化且相对连续、建筑形态多样、建筑密度较城内稀疏的环绕林荫大道(城墙)以外的城市复合体跃然成型。 按照法国的传统定义,城市是指一个连续的空间。林荫大道以内的城市和环绕林荫大道以外的城市复合体共同构成了如流动的盛宴一样的既传统又开放、既浪漫又现代的巴黎,隐性的带有封闭意味的城墙变成了明显的开放。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