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孙江 一分钟的沉默,也是记忆之场(1)


《记忆之场》
主编:皮埃尔·诺拉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靖国问题》
作者:高桥哲哉
版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作者:杨·阿斯曼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论集体记忆》
作者:莫里斯·哈布瓦赫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
主编:孙江
版本:中华书局,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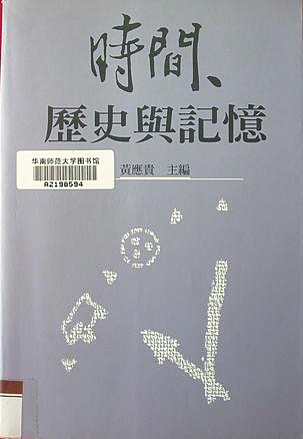
《时间、历史与记忆》
作者:黄应贵
版本: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

《新史学 第8辑 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
主编:陈恒,耿相新
版本:大象出版社,2007年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主编: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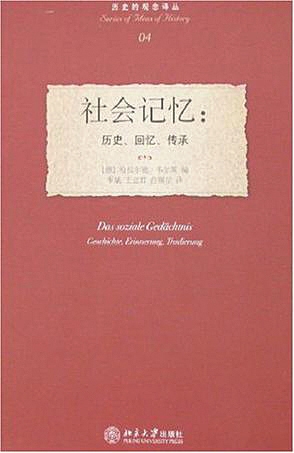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
主编:哈拉尔德·韦尔策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句诗词是谈论“历史与记忆”这个话题时,孙江教授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回乡偶书》在孙江看来并非一首该给儿童念诵的古诗,它讲的是“过去之‘在’”,时间与空间流转,过去在当下留下了痕迹。“过去和现在发生了一个交错,我们的历史书写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孙江在关于《记忆之场》的讨论会上说。
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是《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的主编,与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新史学”研究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和一行历史研究者共同创办了“新史学”丛刊,探讨的问题在国内历史学界具有很高的前卫性。他的历史研究方法贯穿人文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研究主题涉及政治思想史、社会史、概念史等,“历史与记忆”也一直是孙江关注的领域,并在“记忆研究”领域进行了本土化的实践,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可观的影响。
借《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之际,《新京报·书评周刊》围绕着“历史与记忆”问题,与孙江展开了对话。
让历史告诉未来,其实只对了一半
新京报:诺拉创造了“记忆之场”概念,其中的“场所”指涉留在当下的历史痕迹。可以谈谈这些“记忆之场”这个概念,以及它对于重构历史的作用吗?
孙江:“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的词汇,由场所(lieux)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来源于拉丁语loci memoriae。场所和记忆是建构历史叙事的重要元素。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Cicero)在《论演说家》中提到一个名叫西蒙尼德斯(Simonides)的古希腊诗人,此人号称“记忆天才”,他利用“场所”和“形象”的记忆方法,从记忆场所出发,一步步迈向回忆的场所,再现事件。
场所是事件发生地,但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带有重构性特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记忆的场所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可以感知的经验对象,又是抽象的创作,记忆的场所既指实际的自然空间中的场所,也可以是象征和仪式。诺拉认为,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等,因其成为仪式中的对象,从而走进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可以被视为象征的极端例子。记忆和历史相互影响,彼此作用。与历史的实在指涉性不同,记忆之场并没有具体的所指对象,它只是一个指向自身的符号。记忆的场所有三种特征: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
新京报:我们当下通过“场所”所窥到的事件,离历史真实总是有距离的。
孙江:一般认为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我们离真相愈来愈近,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很容易成为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同谋,陷入修正主义者的陷阱中。
比如,几十年来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并没有因为新资料的不断发现而戛然中止,这说明历史/事件不仅仅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还涉及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领域。在涉及权力博弈的历史问题时,有时候历史学者应该退场。
就“记忆之场”而言,历史学者的退场,意味着场所不再是当下叙述中的客体,而是有主体性的记忆。我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其实只对了一半,因为历史或场所不仅仅是客体,它们是有话语权的。恰如历史学家卡尔(E.H. Carr)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诺拉告诉我们要倾听历史的声音,而不是随意增减其意义。
记忆是历史的一部分吗?
新京报:如何理解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孙江:我想强调的是,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是指那种记忆与历史浑然一体的时代结束了。这涉及记忆和历史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记忆与历史是对等的,还是记忆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诺拉继承了记忆理论大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看法,他认为记忆与历史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尖锐地批评诺拉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可以感知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见证人正在消失,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围绕战争记忆的争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新京报:诺拉研究了很多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象征符合,可他为何反对“纪念”?
孙江:诺拉虽然组织了大规模的记忆研究,但他反对相关的历史性纪念,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他之所以开展记忆研究,是出于对当下流行的历史学,特别是年鉴学派等新史学的不满,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忽略事件性,在诺拉看来,这无疑是对事件史的一次“十字军东征”。与此相关,年鉴学派重视中世纪晚期(前近代的历史),忽视当下,它虽然也含有心态史研究,但心态史关注的是过去的积淀和作用,而不是当下具有再生产意义的记忆;记忆的历史是与过去保持连续性,并由现实的集体所承载的历史。
对“记忆之场”的研究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和神话的表层。然而,与诺拉的主观意图相反,随着前两部《记忆之场》(共三部)的成功出版,“记忆之场”一词被人们广泛使用,逐渐沦为单一性、物质性纪念场所的代名词。诺拉无奈地说道:“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其实,《记忆之场》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困境,原本打算解构以往法兰西历史叙述的图景,无意中却重构了一部整体的法兰西历史;原本打算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终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式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下转B04版)
书单推荐人:孙江

